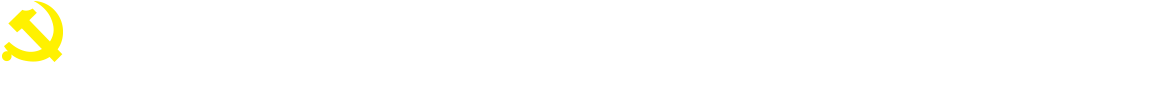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长城与古城
巴彦淖尔境内的长城,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年代久远,故事多。千百年来在河套大地上演绎的蒙恬修长城、屯垦戍边,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历史印记均与巴彦淖尔古长城有关。各个时代不同,长城的建造手法也各有不同,赵长城、秦长城、汉外长城各有特点。多数长城处于险胜之地,伴随其它文化遗址,且具有探秘性,留下许多历史之谜。
赵长城与高阙塞
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乌拉山南麓,有一段赵长城。该长城傍阴山山脉的东端大青山南麓蜿蜒经包头进入乌拉特前旗境内,东起乌宝力格嘎查东端,与包头市哈业胡同乡交界处为起点,蜿蜒向西,到乌兰布拉格沟口指导蓿亥一带渐渐消失,在乌拉特前旗境内总长52703米。底宽6-8米,顶宽3-5米,残高1-3米不等,多数墙体因常年泥土淤泥被深埋地下,地表形成高1-1.5米的土垅状剖面。
河套及南流黄河以东地区,自春秋以来,本是林胡、楼烦共有的游牧之地。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赵武灵王(前325~前229年)二十年(前306年),也曾“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
进入战国中、晚期,赵武灵王再次北征林胡、楼烦,将赵国的势力拓展到了阴山西段的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的山前地带。《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所筑长城,起自“代”,即今河北省蔚县境内,沿洋河进入内蒙古兴和县,经卓资山抵阴山脚下,沿阴山南麓向西延伸,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包头市郊区、乌拉特前旗白彦花乡的乌拉山南麓,至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的达巴图沟(当地亦称大坝沟)口西侧为止。
很长时间以来,有关赵武灵王所筑之高阙的位置,史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同巴彦淖尔市文物站的业务人员,多次沿阴山南麓的赵长城向西追踪调查,在乌拉特后旗狼山南麓的达巴图沟口西侧,发现了赵长城最西端的长城遗迹及高阙的位置。调查证实,赵长城由东向西,蜿蜒在阴山西段的狼山南麓,在达巴图沟口两侧仍留有长城的遗迹。
高阙塞故址位于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那仁乌博尔嘎查北侧山脚下,古城夹在东侧的达巴图沟和西侧的查干沟的台地断崖之上。地表现存古城由南北两个小城组成,北城略呈方形,南城为长方形,北城内发现有较大的房址6座,南城内亦发现石砌房址遗迹。两个小城的修建风格明显不同,反映其并非同时代一次修筑。故推测该古城北侧的方形小城,即是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所筑之高阙塞无疑。而南侧较大的石城,当是在汉代沿用时重新扩筑,防御的重点仍然在较为高大坚固的北城。高阙塞的东北方向是宽阔的达巴图沟口,西南是查干沟口,城址位于两沟的交汇之处,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为绝佳的军事要塞。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高阙:“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高阙也。”临戎城遗址在今磴口县补隆淖乡西南,即河拐子古城。以此地山势及与临戎古城相对地理位置推测,该古城北侧的方形小城,既无瓮城又无角台,与汉代建筑的边塞城防建制明显不同。因此,该小城及城外的石墙,即应是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所筑之高阙塞之塞墙。而南侧较大的石城,当是在汉代沿用时重新构筑。
秦长城
秦长城巴彦淖尔段由包头固阳县北部的王如地起,沿阴山山脉进入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以增隆昌村东端为起点,西以圐圙补隆村西北10公里处的贾力盖沟(扎拉格河)进入中旗,沿查石太山向西经色尔腾山、狼山向西进入乌拉特后旗。该段长城在巴彦淖尔市境内总长度255.67公里,其中在乌拉特前旗境内长度为79公里,在乌拉特中旗境内长度约166公里,在乌拉特后旗境内长度10668米。
秦长城修建在阴山北坡,有部分初为战国时赵国所修。该段长城皆为石块建筑,截面呈梯形,一般顶宽为3米,基宽为3.5米,高2.3—6.5米。在长城南侧较平缓的山脊上,约每隔300—500米就有一个石垒烽火台,沿线烽燧障塞较多。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于漠北,收河南地,渡河居阴山、北假地,因险筑塞,修筑长城。为巩固北部边防,借助原战国赵、魏、燕等国的北部原有变成构筑连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长城万余里,以防匈奴的南进侵扰。
正当中原进行着秦的统一战争而无暇顾及北边之时,匈奴再次南下占据了河套地区。此前,自赵武灵王北筑长城,从河套地区驱逐林胡、楼烦后,林胡在文献中就突然消声匿迹了。
1961~1964年,蒙古和匈牙利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的呼尼河谷北岸发现了一批匈奴墓,这些墓葬和呼尼河谷其他匈奴墓不一样,属于竖穴土坑墓,未见葬具,随葬品有陶罐、马衔、马镳、箭头、弓弭、漆器等,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这类墓葬的形制,与发现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相同,据此有学者推测,呼尼河谷北岸墓葬的墓主人,可能是来自河套地区的游牧部族的后裔。从赵武灵王北征的路线看,林胡在楼烦的西北,那么分布在鄂尔多斯西北的春秋战国时期竖穴土坑墓,就有可能是林胡的遗迹。
匈奴形成后,在其四大异姓部族中有兰氏部落。据此可以推测,自赵武灵王北筑长城后,林胡可能越过阴山,北上游牧到了漠北的鄂尔浑河流域,并加入了匈奴的军事大联盟,成了匈奴四大异姓部落的兰氏部落。林胡之“林”与匈奴异姓贵族兰氏之“兰”的读音非常相近,恐非偶然。也许是林胡投奔匈奴之后,在文献中就此改头换面,皆以匈奴身份出现了。此后到秦汉之际,出现在史籍中的就只剩下“楼烦白羊王”之属。这很可能是,居于林胡之东的楼烦在林胡北遁之后,于秦汉之际逐渐入居了原林胡占有的河套地区。其后,这支“楼烦白羊王”很可能也成为了匈奴的别部。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它与韩、赵、魏、楚、燕、齐七国争雄的局面,建立秦王朝。秦统一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以前更为频繁。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由于头曼单于不断南下侵扰,秦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匈奴败撤,秦军夺取河南地。匈奴被迫北却七百余里,从阴山以南退居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带,内蒙古中南部阴山之南尽纳入秦的版图。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始皇三十三年,秦又把原秦、赵、燕三国在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筑成万里长城。
秦朝所筑之长城,在历代长城中是最为科学的。秦长城修筑在阴山和燕山山脉的北坡较高处,居高临下,因山为险,易守难攻。
秦朝在北边新开拓的领土上,分别设置云中郡(原赵国云中城,今托克托县古城村)、九原郡(原赵国九原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上郡(约在今鄂尔多斯市南部)、雁门郡(约在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等郡县,移徙内地居民屯垦戍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塞外列城与光禄塞
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当时,匈奴乘秦末农民起义的混乱时机,夺回了此前秦占领的阴山及其以南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在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先后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网,北服丁零各族。后又消灭楼兰、乌孙、乌揭及其周临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建立了一个以漠北为中心的庞大奴隶制政权。匈奴单于庭设在头曼城,政治军事中心,约在今乌拉特中旗境内的狼山中。
西汉初年,匈奴成为汉王朝最大的威胁,曾屡次南下寇边。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扰,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击匈奴,在平成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被匈奴围困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密计"以重金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脱。“白登之围”后,刘邦采用娄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始,汉朝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汉武帝派马邑人聂壹,诱匈奴单于取马邑,又命李广、韩安国等率兵三十余万埋伏于城外,俟机出击,但被匈奴识破,引兵而去。此后,经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遂取河南地”。卫青击败了乘楚汉相争重新盘踞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夺取河南地,汉在此立朔方和五原二郡,并移民屯边,穿渠引水,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建设。又经元朔五年(前124年)至六年的漠南之战;元狩二年(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汉武帝大败匈奴,迫使匈奴退至漠北草原。汉朝自此在东面夺取了匈奴左地,西面拆散了匈奴与月氏的联盟,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此后,匈奴左部迁到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直对汉云中;右部迁到蒲类海(今新疆哈密西北巴里坤湖),直对汉酒泉、敦煌。单于的主力则直对河套地区的五原至鸡鹿塞一线。
汉王朝自北击匈奴起,便在阴山、燕山南麓兴筑长城,作为防御匈奴南下的屏障。考古调查发现,在今河套地区可见汉代增筑的长城共有三条。其中最南的一条位于乌拉山南麓,东起自包头市昆都仑沟口附近,向西至乌拉特前旗西山嘴卧羊台;另外两条则位于阴山以北的戈壁荒漠地带。史载,太初三年(前102年),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河名,在今蒙古国境内),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在阴山以北的考古调查发现,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有南北两条,两条长城相距5--50公里不等,亦称汉外长城。其中靠南的一条东起今武川县境内,经固阳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伸入蒙古国境内;靠北的一条,东起武川县境内,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穿越蒙古国,再折向西南,与今额济纳旗境内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筑的居延塞即汉代烽燧线相接。
就目前考古调查的发现,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位于阴山以北的这两条汉外长城及所附之边堡,即是汉代文献所载之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
汉长城南线经由达茂旗进入巴彦淖尔市境内,经新忽热、巴音、乌兰、川井等地向西进入乌拉特后旗,在巴彦淖尔市境内总长度318.71公里。其中在乌拉特中旗境内长约183公里,沿线有67个障塞、27个烽火台;在乌拉特后旗境内长度为135.71公里,沿线有13个古城城墇遗址。
汉长城北线亦经由达茂旗进入巴彦淖尔市境内,经桑根达来、巴音乌兰、川井进入乌拉特后旗,在巴彦淖尔市境内总长度340.56公里。其中在乌拉特中旗境内长约186公里,沿线有4个障城遗址;在乌拉特后旗境内长度为154.56公里,沿线有4个障塞。
两条汉外长城为并行的两道墙体,南北间距为10—50公里,从乌拉特后旗出境,延伸到蒙古国南戈壁省,被蒙古国称为“成吉思汗边墙”。墙体大部分土夯筑,经历两千多年的风蚀雨剥,现大部分地段已成为土垅状,有部分地段基本上没有长城踪迹了。
就现场观测,这两条长城无论从构筑的规模及实际达到的高度,不足以作为一道屏障阻挡匈奴的骑兵。因此可以推断:汉武帝时,汉朝原本期望在秦始皇长城以北修筑长城,将匈奴阻隔于阴山以北的戈壁之上,但是,此地乃无草缺水的荒凉之地,又皆筑长城之材料匮乏,故而仅仅就地取材,修筑了两条低矮的墙体,根本没有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再加此地远离粮食产区,粮米供应自然十分困难。因此,这两条长城应当是没有完工即已放弃的军事工程。在阴山北坡秦长城的内侧,考古调查曾经发现了汉代的烽火台和居住址,以及汉代的铁甲片和箭头。说明,汉代最终还是把对匈奴的防线后撤,放在了更为理想的秦长城一线。
战国、秦汉时期,往往将长城统称为塞或障寨,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兴筑的赵北长城,称“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派遣蒙恬北逐匈奴“因河为塞”,汉武帝派遣苏建“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等等,都是指长城,也称做塞墙。在长城沿线的山谷口或平川地带每隔数十里兴筑的小城,称为障,由候官驻守,故又称为候城。在山中兴筑的瞭望和防守据点叫做亭。在重要山谷口和交通要道上兴筑的防守据点叫做塞。在重要交通要道上兴筑的据点,有时也称为关。在长城沿线及各城障之间,筑有一系列的互相可以瞭见的烽火台,统称为烽燧或燧。各城、障、塞、关、亭、燧都有自己的固定名称,如遮虏障、望亭、鸡鹿塞、化胡燧等等。有固定专有名称的塞,仅是长城沿线上一处独立的军事防御设施,有时容易与总称长城为塞的塞相混淆,造成误解。
光禄塞,本来的含义应当是指汉外长城,即是由汉光禄勋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故称光禄塞。《汉书·地理志》五原郡固阳县下注有:“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呼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此处所言之光禄城,应是指光禄勋徐自为驻守的城,而不是通称长城的光禄塞,其余四座城名,应是光禄塞上不同城障的名称。
在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政府以东约15公里的大十份村,北距马鬃山秦汉长城直线距离约2公里处,有一座增隆昌古城。增隆昌古城与增隆昌水库(又称白山水库)相邻,现可看到城墙的轮廓,城墙内有不少西汉年间遗留的陶器碎片,东部有同期墓葬,城址周围分布有居落遗址。城北两公里便是东西横亘的秦汉长城。因其地理位置,对照文献记载,推测这座古城可能是汉代光禄城故址。光禄塞在西汉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防御作用,曾有效遏止了匈奴的南侵。
另据考,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史记·匈奴列传》)。即在五原郡长城边塞外,阴山石门水(今内蒙古昆都仑沟)峡谷口,修筑光禄城等军事城障,以控扼汉、匈之间南北重要交通的石门水谷道。城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明暗乡小召门梁古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因光禄城南临长城边塞,故称为“光禄塞”。《汉书·匈奴传》: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即此。
此外,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宁乌素嘎查发现的石筑长城西南近1公里处,是朝鲁库伦古城。朝鲁库伦是蒙古语石头城的意思,是该旗境内光禄塞南线上最西端的一座障城。考古发现该城构筑坚固,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因此或许可能是汉宿虏城遗址,但目前尚需作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
光禄塞建成后,曾在军事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保卫了汉朝北部边郡的安宁。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就是从外城进人朔方郡,再经西河、上郡而至长安城,觐见了汉宣帝。呼韩邪自长安返回漠北时,曾自愿请求留居漠南的光禄塞上,以共同保卫汉朝北部边境地带的安宁。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后宫良家女王嫱(昭君)自愿请求嫁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封其为“宁胡阏氏( yānzhī )"。从此以后,汉朝的北部边境局势更加稳定,汉朝削减守卫外城的大半兵卒,节省了大量军事开支。长城内外形成了社会生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交流不觉,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的大号局面。这种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
北魏长城
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乌拉山北麓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巴音温都尔嘎查大坝沟与阿拉奔水源地之间新发现石砌和土筑两段长城。石砌长城走向由大坝沟口东烽火台起,沿大坝沟沟东向西南断断续续延伸,约3000米,基宽2—3米,残高1—1.5米,多为石块垒砌。土筑长城位于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白彦花嘎查,从大坝沟西北起遗址向西北延伸约9000米(其中有1000米消失段),至阿拉奔南水源地前消失。此段长城基宽3—6米,残高1.5—2米。据当地老乡介绍,此长城一直向西延伸至乌梁素海西岸还有迹象。
鸡鹿塞
鸡鹿塞古城位于沙金套海苏木的巴音乌拉嘎查所在地北2公里哈隆格乃山口西侧,建筑年代无确切记载。哈隆格乃山沟可直通汉时匈奴占据的漠北地,山沟较平坦、宽畅,是阴山南北通道之一,是匈奴率大部兵马入河套进中原的理想途径。
该城全部采用天然石块砌成,筑于距沟底高18米的山坡平台上,呈正方形,边长68.5米,墙上端残存宽度约3.7米,下端厚约5.3—5.5米,残墙高一般为7米,最高8米,西北缺口处只有2米。在城的四角,有突出部类似后来的“马面”。靠南墙东部内侧和西北角砌有蹬道,南墙偏西部有一开口,是城门所在,在城门外有入口的小围墙,是瓮型城门。在城外距城不远处,有一道石砌短墙,虽已塌,但可辨认,这可能是防止山洪冲击该城的防水墙,墙外有一条西北顺山势而下的流水沟,似有人工开掘的痕迹,目的是便于洪水畅流。城内还有些什么设置,现无法弄清。就城址附近发现的陶瓦、箭镞以及城的建筑形式,足可以说明是汉代鸡鹿塞古城遗址无疑。
朔方郡是汉代的北方边郡之一。鸡鹿塞是朔方郡爱在阴山西部长城沿线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又曾是汉与匈奴和平交往的出入关塞。
朔方郡的西北部为阴山山脉,穿越阴山后即进入广袤的蒙古高原。西汉时期,匈奴单于庭设在朔方郡西北方的漠北地区。汉王朝派兵越过阴山北击匈奴时,经常经由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几条路线进军。而经由朔方郡出击时,逾越阴山的主要通道就是鸡鹿塞。
汉朝在阴山山脉的南麓的一些山谷通道及其附近,修筑了一系列的障塞和烽燧。鸡鹿塞作为阴山山脉西部的一处重要的关口,是朔方郡西部都尉治所窳浑县西北方的一座军事据点,距窳浑城约20公里。
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汉与匈奴间的战争状态从此宣告结束。基于呼韩邪单于自己的要求,愿留居漠南光禄塞。其时呼韩邪单于曾途径鸡鹿塞,从此鸡鹿塞载于史册。直至西汉末年的数十年间,北方边郡都是在和平环境中度过的。西汉以后,匈奴再次崛起于蒙古高原。东汉和帝永平二年(90年),汉将军窦宪与匈奴南单于联合出击,经由鸡鹿塞出漠北,大败匈奴北单于,显示了鸡鹿塞亦是作为从阴山以南进入蒙古高原的一条捷径的重要作用。
新莽以后,朔方郡开始进入衰退期。东汉时期,朔方郡治迁到了临戎县,并撤销了窳浑县,境内农业人口大减。公元二世纪中叶,南匈奴再次进入河套,朔方郡治被迫从临戎迁到了五原郡。从此,朔方郡及所属县城全部沦为废墟。鸡鹿塞及其朔方郡,从设置到废弃,共经历了260余年的时光。
在哈隆格乃山谷两侧的拐弯高处,散建有亭燧或亭障,在此谷中有烽台9座,距离不一,大小各异,是作为防御和报警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