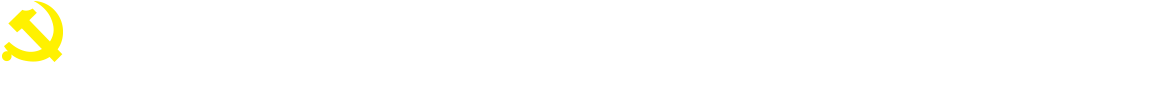河套水利遗产的内涵、历史与价值
1 河套水利遗产的内涵
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在与自然互动共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遗存。比较常见的文化遗产划分是按照遗产存在性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水利遗产是历史时期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在与自然互动共生过程中形成的水利文化遗存。有学者认为,水文化遗产应分为工程和非工程遗产两大类,每一类遗产应有其物质和非物质性态。[1]这种划分的可商榷之处在于,一般人们说到水利工程遗产,就是专指物质性态的水利工程,在水利工程遗产下划分物质和非物质性态,与人们已经形成的普遍认识不一致;同时,非工程遗产的表述有一定的不确指性,非工程是指非水利工程的其他工程和建筑,还是指非物质工程性态的水利精神文化,要有一个确切的划定,不能既指前者又指后者。水利文化遗产首先应以其存在性态是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两大类。水利的物质文化遗产指水利工程及与水利活动密切相关的其他物质遗产。水利工程遗产主要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城市水利工程、运河工程、园林工程等遗产。其他物质遗产主要有宗教建筑、人文景观、生态系统等,包括水利行政、水神崇拜的建筑和遗址以及水利文物,包括水利工程衍生的农业聚落和人文景观,还包括与水利工程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等。水利的精神文化遗产指水利活动的精神文化表现,包括祭祀仪式、文化活动、规章制度、知识技术、档案文献、水利历史、水利艺术、水利故事与传说等。
河套水利遗产指历史时期河套地区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在与自然互动共生过程中形成的水利文化遗产。从河套水利遗产的形成时间看,主要是近代以来形成的遗产。虽然古代河套地区的人们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过程中曾经修建过水利工程,但由于河套地区特殊的地理地貌而极少保存和发现这些工程的遗址、遗迹,同时古代文献也较少详细记载这些水利工程的状况,而河套近代水利工程保存完整、记载较为详细,所以河套水利遗产的主体是近代以来的遗产,这与我国大部分水利遗产形成于古代有所区别。从河套水利遗产的存在性态看,包括物质性态的水利工程、农业聚落、农业景观等内容,也包括精神性态的祭祀仪式、文化活动、档案文献、规章制度、知识技术、水利历史、水利艺术、水利故事与传说等内容。从河套水利遗产的具体内容看,物质性态的遗产主要有:清代道咸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的河套灌水、排水渠网系统,河套近代以来水利开发和走西口移民形成的农业聚落,河套近代以来形成的北方春小麦农业景观。精神性态的遗产主要有:近代以来郭大义、王同春、杨满仓等地商开发河套的历史和事迹,近代河套人民的河神祭祀与河灯节文化活动,河套人民口耳相传的开挖杨家河的故事和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河套人民的“水利抗战”史事,河套人民开挖总干渠、总排干的事迹与精神,近代以来河套的水利档案与文献。
2 河套水利遗产的历史
河套水利遗产的历史即河套水利遗产形成的历史过程,这里主要梳理河套灌水、排水渠网系统的形成过程。河套近代以来灌水、排水渠网系统的形成经历了两百余年历史,可以分为晚清八大干渠、民国十大干渠及建国后河套灌排渠网三个发展阶段。
2.1 晚清八大干渠
晚清河套地商开发了八大干渠,分为道咸和同光两个时期。道咸年间河套的水利开发主要是永济渠(缠金渠)和刚济渠(刚目河)。道光五年(1825年),甄玉、魏羊从黄河开口修成缠金渠。道咸年间开发缠金地的商号有四十八家,缠金渠接挖至一百四十余里,灌地三四千顷,收粮十万石。缠金渠后改名永济渠,是河套地区最早的人工干渠。咸丰年间地商贺清在黄河天然支流刚目河基础上开濬刚济渠。清同光时期是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高潮时期。同治八年(1869年),郭大义开挖短辫子渠,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同春为渠头重新开挖短辫子渠,渠成后改名老郭渠,民国改称通济渠。同治十一年(1872年),侯双珠等开挖长济渠。光绪初年,地商樊三喜等修挖塔布渠。王同春分别于光绪六年(1880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开挖义和渠、沙河渠和丰济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将后套各大干渠归公。此时河套形成了八大干渠,自西向东为永济渠、刚目渠、丰济渠、沙河渠、义和渠、长济渠、通济渠及塔布渠。
2.2 民国十大干渠
民国河套水利的主要成就是新增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条干渠和扩建沙和渠。黄济渠原名黄土拉亥河,是河套西部原南北河之间的一条天然河流,因渠口有黄土脑包一座,得名黄土拉亥河。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教会以赔教款名义,全部占有黄土拉亥河渠地。民国十四年(1925年),临河设治局将黄土拉河渠地无条件收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黄土拉亥河改名黄济渠,列为河套十大干渠。民国六年(1917年)春,河曲杨氏开挖杨家河,工程历时十年之久,费银七十余万两,计干渠全长一百四十余里,列入民国河套十大干渠。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民国政府修整乌拉河,由傅作义派出官兵七百余人,两个月完成全部任务。经过这次大规模修正后,乌拉河灌溉面积达二十至四十万亩,列为河套十大干渠。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夏,傅作义派军工万余人扩建沙和渠上部,经五十余天施工,完成土方一百三十多万立米,当年增灌面积达到三十万亩。从此,沙和渠改名复兴渠,列为河套十大干渠。[2]
河套灌区的形成,经历了由八大干渠到十大干渠的演变过程。原来的八大干渠大体于清末基本挖成,到了民国时期,刚济渠和沙和渠均被合并到大干渠成为支渠,又先后挖成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和复兴渠。最后演变成的十大干渠是:乌拉河、杨家河、黄济渠、永济渠、丰济渠、复兴渠、义和渠、通济渠、长济渠和塔布渠。至1949年之前,河套水利遗产主要是以十大干渠为主的灌水工程。
2.3 建国后河套灌排渠网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主要水利工程有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总干渠工程及总排干工程。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位于磴口县巴彦高勒东南黄河干流,在黄河上建立拦河闸,实现拦河截水、截流灌溉功能。拦河引水工程由拦河闸和土坝连接组成。拦河闸从黄河左岸向右岸延伸,闸分十八孔,孔径十六米,闸身长三百二十五米。枢纽工程包括北岸总干进水闸、南岸进水闸、沈乌进水闸等八项工程。1959年6月工程动工,1961年5月截流告成。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结束了河套灌区自流灌溉的历史,成为建设新型大灌区的起点,是河套建设1000万亩粮食基地的根本水利设施。[3]总干渠是指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北岸输水总干渠,就是将河套各大干渠的引水口都归并到总干渠引水。1958年11月根据“一首制”方案开始施工,包括进水闸、跌水电站、四个分水枢纽、总排干与总干渠交叉工程等工程。总干渠是政府组织群众人工开挖,到1967年与三湖河干渠接通。总排干是河套灌区排水系统的主体工程。总排干前身是黄河故道乌加河,是灌区排泄灌区余水、山洪水、地下水的天然通道。总排干主要解决河套灌区的排水、排盐碱问题。工程包括总排干主干段、乌梁素海及出口退水渠三部分,从1957年开始,1967年初步完成,以后又经过七十至九十年代年的大规模改造扩建。
新中国以来,河套灌区建设了三盛公水利枢纽、总干渠工程,同时从黄河上引水的小干渠与十大干渠合并,形成十三大干渠,即一干渠、乌拉河、杨家河、黄济渠、永济渠、丰济渠、灶火渠、沙和渠、义和渠、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和三湖河。由三盛公水利枢纽、总干渠、干渠组成引水系统,由总排干及干沟组成排水系统,两者共同组成河套灌排系统,这是河套水利遗产的主体。
3 河套水利遗产的价值
水利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生态价值等方面。水利遗产的特点不同,价值体现也不尽相同,有的水利遗产具有某个方面的价值,有的水利遗产具有几个方面的价值。河套水利遗产则具有五个方面的价值。
3.1 经济价值
河套水利工程是河套经济的命脉。河套农业对水利的依赖就像鱼依赖于水,没有水利就没有作为农业区域的河套。河套地区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交界地点,年降水量约在200毫升左右,引黄灌溉的作用尤其突显。目前河套农田约800万亩,全部依赖于引黄灌溉。河套地区工商业和服务业不发达,农业是主要支柱产业。从河套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区特点、产业布局等情况看,可以预计未来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河套的农业在整体经济中仍居重心地位,黄河水利仍然是河套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
3.2 历史价值
河套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河套自古是农业和牧业交界地带,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域,近代以来由于大规模开发水利而转变为农业区域。水利开发在近代河套历史变迁中起决定作用,没有水利开发就不可能改变河套游牧为主的历史,就不会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河套平原。河套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水利开发史,水利开发已经成为河套的集体记忆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河套水利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既是河套开发的历史见证,又是研究河套历史变迁的物质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河套水利开发与农业发展是冯玉祥五原誓师的主要背景因素,河套农田水利是傅作义绥西抗战的基础和保障,这些近代河套历史事件都与水利休戚相关。
3.3 文化价值
河套水利遗产的文化价值在于,水利是河套文化的标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河套的文化精神。河套文化是西北边疆农业文化,既有近代农业文化的一般特点,又有河套地区的特殊性。河套水利文化与移民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农业文化及饮食文化等一起构成河套文化,同时水利文化又贯穿和渗透在河套文化方方面面之中。随着河套的水利开发,北方各省人民移民河套,既成为河套水利开发的主力军,又作为河套水利开发的受益者。河套近代移民史就是河套近代的水利开发史,走西口移民文化、民俗文化与水利开发密不可分。旅游业是近年河套新兴的产业,从水利遗址说,三盛公水利枢纽等水利工程具有观赏价值,而河套人开发水利的故事也颇具文学性和艺术性,这些都是较好的旅游资源。农业文化、饮食文化也都是建立在水利开发建设的基础之上。
3.4 科学价值
河套水利遗产的科学价值至少有:民修阶段的河套水利工程,王同春等掌握了从黄河开口引黄灌溉、在黄土上开挖干渠的技术,在还没有现代测量技术的背景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科技;河套八大干渠、十大干渠的渠线走向为从西南向东北成四十五度角,是完全符合河套地区的地形地貌的设计;早期河套水利工程将黄河故道乌加河作为天然退水渠,灌溉余水经乌加河入乌梁素海,再流入黄河,形成完整的循环利用;河套人民在长期水利实践中摸索出的“草闸”,是河套地区独特的节控水技术;建国后建设的三盛公水利枢纽、总干渠工程是世界上“一首制”的代表工程;以总排干及干沟构成的排碱系统,有效的起到改良盐碱地的作用,对农业增产增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3.5 生态价值
河套水利遗产的生态价值在于,有效地阻挡乌兰布和沙漠向东扩张,在黄河北岸的塞外地区建立起绿色长廊,这在北方干旱少雨地区非常少见,因此河套平原有“塞北江南”之美誉。如果不是在河套地区发展农业和植树造林,可能乌兰布和的风沙已将这块地方变成沙漠。河套灌排系统之于河套平原,就如坎儿井之于新疆盆地,是绿色与绿洲之母。河套平原面积辽阔,土地肥沃,引黄灌溉,不但是我国北方春小麦重要产区,还出产独具特色的农业产品,如华莱士、河套蜜瓜、西瓜、向日葵、玉米、番茄等,发展生态农业有巨大潜力。
河套水利遗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水利遗产,河套水利遗产的内涵、历史与价值都有相当的独特性,但因为河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河套水利遗产还没有被足够重视。相信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河套地区的落实,随着河套地区文化建设的进步,尤其是随着河套灌区申请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推进,河套水利遗产的价值将被全世界所认识。(刘勇 苏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