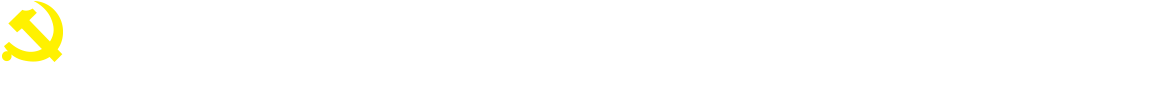河套灌区 从始创孕育到蜕变形成的发展过程
内蒙古河套灌区作为我国的古老灌区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始于秦,续垦于汉,中兴于北魏唐,历经兴衰,成于清末,盛于新中国。对于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河套灌区来说,没有水就不适于人类生存,没有水利就没有灌溉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也无从谈起。水资源是河套灌区农业循环链条上的核心资源。河套地区的灌溉农业活动既利用了当地特定的自然条件,也受到了自然环境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使其在开发方式、过程、发展方向和效果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因此,河套灌区的开发史也是一部农业开发的治水史。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将河套灌区推向历史舞台的根本
河套灌区为黄河冲积、洪积平原,地平坦,渠纵横,土肥饶,米粮川。灌区位于黄河“几”字弯上方,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西与乌兰布和沙漠相接,东至包头郊区,黄河从其南穿流而过,阴山从西向东屏立其北,东西长260余公里,南北宽60余公里。按区位地貌特征由西向东分为乌兰布和灌域、后套灌域、三湖河灌域。乌兰布和灌域位于河套灌区的西部,灌域内星罗棋布的分布着高低不等的沙丘,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地面坡降1/3000-1/5000,地面高程1048-1036;后套灌域是河套灌区的核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东西向地面坡降1/5000-1/8000,南北向坡降1/4000-1/8000,地面高程1050-1090;三湖河灌域位于乌拉特前旗东部,介于乌拉山南麓与黄河之间的东西走向狭长灌域,南北宽5公里,地势西北向东南倾斜,地面坡降1/7000左右,地面高程1018-1010。河套灌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特殊地形特征,为灌区开发提供了特有的发展方式。因此,可以想象,河套灌区就是阴山山脉用臂弯拥在怀中的一方热土,黄河是其用双手捧起的金色哈达。
地处北方与中原结合部的河套地区,联通南北,纵贯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阴山、黄河是河套地区地理分界线上的核心组成部分。阴山横亘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草原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清中叶以前河套的后套地区处于南北河之间,黄河因阴山阻挡绕套区而行,其西、北、东、南四面环以黄河。黄河入套后坡度较小,水流平缓,南、北河溢流岔河众多,通河便利,土地富足,可耕可牧,便利的引黄灌溉条件,发展农牧业成为必然。这里依山阻河,形势险要,粮草丰茂,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占据河套,可以作为根据地,“风吹草低见牛羊”,养兵牧马的天然牧场,南望关中,逐鹿中原;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来说,“不教胡马度阴山”,屯兵固边、休养生息的天下粮仓。河套灌区的这种地形在世界大江大河里绝无仅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既适合游牧又适合农耕的风水宝地。
二、黄河南北河变迁是河套灌区孕育而生的基础
河套地区的发展进步与水息息相关。黄河流经河套灌区后受到阴山利导,在河套灌区顿足绕行,提供了富足的水源,融合地理环境的光、热和土壤条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发展传统农业提供了开拓空间。依水而生、逐水草而居的先民随着黄河的变迁不断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趋利避害,使河套灌区在不断的变革中孕育而生,经过逐步改造规模也不断扩大。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黄河流域的农业活动方式由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决定。《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呈现出一派荒漠草原的游牧自然景观。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的垦殖主要聚集在黄河北河以西的乌兰布和沙区一带。《水经注》记载,黄河由银川平原出青铜峡沿贺兰山取东北向,经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二十里柳子进入河套灌区,分成南河、北河。南河向东分流,即现今黄河主河行河;北河,即当时黄河主河(现今乌加河也称总排干沟),继续北流,前行20余公里后受阴山山系阻挡沿山前台地折而东流,流经200余公里后,又受乌拉山地形阻挡形成90度向南拐头,与南河相汇,复向东流。台地与北河之间形成了宽约5公里左右的狭长灌域,系山前洪积扇平原,仍是土壤肥沃的可耕田,属“北假”范畴。在清同光年以前,黄河仍处于冲刷时期,南、北河受自然冲刷淘岸,相向溢流众多,两河之间仍处于湿地状态。清中叶以后因北河上游淤塞,南河成为主河,河岔流向与河套平原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相吻合,北河断流后逐渐成为山洪水与南河岔河的退水渠道,为灌区提供了排水出路,得天时、地利之便为灌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条件。由于黄河南、北河的变迁,在阴山以南,黄河“几字弯”以北的南、北河之间,自然形成了“引河溉田,得自然之力”能灌能排的千万亩大型灌区。至此,河套也有了黄河以南为前套,以北为后套之分,河套灌区也应然而生。
三、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是河套灌区蜕变形成的直接动力
两千年以来,河套地区就随着朝代的更迭先后开始了以秦王“发谪徙边”的“北假”营田,西汉“抵御匈奴”的屯垦戍边,北魏“富国强军”的五原屯田,唐朝“筑城固边”的丰州开渠,清初“春种秋回”的雁行耕地,清末“资本积累”的地商开发等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引黄灌田开发。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贯穿了河套灌区农业水利开发的发展过程,也先后演进了北部开发、西部开发、东西部结合开发和以中部为核心的全范围开发。这些闪光历史节点的关键时期,灌区完成了从始创孕育到蜕变形成,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跨越。
“北假”营田:河套平原土壤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史称“土皆膏腴”,灌区的萌芽开发始于“北假”。《水经注》载: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往,皆北假也。在秦汉时期,现河套大部,黄河处于冲积时期,不宜耕种。一是水无定所;二是盐碱化较重。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河南地”(包括今鄂尔多斯地区):“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集解)》有注释:“其地多水泽,又有卤。”卤,就是盐碱,不利于植物生长。《汉书·匈奴传》“泽卤非可居也”。因此,这一时期河套地区开发主要集中在黄河泛滥区外围“北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又北渡黄河,北逐匈奴,据阳山(今阴山)北假中。攻取高阙、陶山(今狼山山脉)、北假,并筑亭障守卫,驱逐戎狄。将北河(乌加河)榆中(今准格尔旗一带)三万多户迁居北假一带,实行“发谪徙边”“鬻爵垦殖”的边地政策,设置田官,开河引水,促使土地开发和水利开发得到发展,“徙边北河榆中”也是河套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移民垦殖的开始。
西汉屯垦。汉朝为巩固河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带动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史记·平淮书》:“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从河套至甘肃西北部一带以“军团”形式开展屯田士卒达六十万之众,数十万军民的大迁徙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这也是官办水利在河套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发展。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徙民屯田,皆予犁牛”,没有收获之前,还“予冬夏衣廪食”。“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文献通考·田赋二》:“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汉书·河渠书》“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也是史书对河套灌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现实描写。从考古发现,现今乌兰布和沙区东缘(乌兰布和灌域)是西汉屯田的主要区域之一。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河套地区“人民帜盛,牛马布野” [1],成为汉王朝进击匈奴最重要的粮草、军马供应基地。西汉屯垦推动了河套地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集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碰撞、交融中相互转化与渗透传承,既开拓经营了这片土地,又巩固壮大了西汉王朝,既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又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北魏军屯。北魏时期,统治者以“屯田”的方式使河套灌区重新换发了活力。屯田,就其经营形式而言,是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按照一定的组织系统,强制军队或平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屯田在具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下,还要具备两个客观自然条件,一是大片荒地;二是水源问题。河套地区两者兼具。
北魏政权在复兴西汉屯田的同时,将官办水利的措施进一步强化,实行计口授田,分给耕牛,奖励垦种,设置“八部帅”,劝课农耕,实行监督管理,大力推行屯田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史载有著名的“五原屯田”“通渠灌溉”和“枝渠东出”,灌溉规模近百万亩,主要分部在东部与西部。“五原屯田”指在今包头以西、乌拉山以南的三湖河平原和阴山以南,乌加河以北,都在北河沿河一线,颇收灌溉之利。北魏统一北方前后,拓跋珪曾于登国九年(394年)在河北五原(河套)到稒阳(固阳)一带屯田。《魏书·太祖纪》“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拓跋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阳塞外。”《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公元488年),魏孝文帝于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六镇是北魏在沿河流域设置的军事重镇,现今的河套灌区属沃野镇管辖。在北魏时,除“五原屯田”之外,在乌兰布和灌域也进行了农业种植,这一地区也属汉代垦区。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北魏地图分析,“枝渠东出”的走向正在这一区域。这一时期,北魏借助河套地区有利的水土资源开渠引灌,体现了从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向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经济转变的鲜明特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推动了河套灌区水利开发的规模式发展,北魏政权得以休养生息,也为北魏改革大业奠定基础。
丰州开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河套地区或为战场,或为牧场。直到隋末,也有水利屯田,但规模不大。到了唐代,河套灌区属于关内道设丰州,治所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南部),筑受降城,为了解决驻军给养,河套灌区又一次成为重点屯田地之一,又进入农业水利开发的新阶段。
史料记载,唐代为了加强对水利的统一管理,在全国颁布《水部式》,以统一法令,内设专管机构都水监,其下由都水使者,掌管修渠和灌溉事宜,以加强流域的统一管理、同步治理。宁夏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是京城长安之所在地区,也是黄河流域农田水利最发达的地区。唐高宗永徵四年(公元653年)开有陵阳渠(丰州九原)。《新唐书·地理志》载:“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又载:“有咸应、永清二渠(在现今五原县南西小召一带),贞元中(约公元796-803年)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李景略,唐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防御使。据清《五原厅志略》载:“丰州穷边气塞、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与土卒同甘苦,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二年之后,储备充实,雄于北边,卒赠工部尚书”。
清陈履中《河套志》记载:“丰州屯田娄师德、唐怀景、李景略、卢坦最有名”。丰州开渠不仅有效推进了水利灌溉事业的规模,而且促进了唐王朝军力强盛,粮食供给,促进了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
“雁行”开发。在清康、雍时期,内地人民开始越过长城,深入大漠,进入河套,来到黄河的支流河岔间开荒种地,春种秋回,这种流动耕种方式称为“雁行”。由于当时河套尚未穿渠引水,垦种也随河岔“随波逐流”,收成多无把握,此时蒙地禁垦,开发还不成规模。
河套清代的农业种植,以明末清初的“雁行”流动方式种植持续了近百年时间,为河套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雍正后期雁行定居开发开始,道光、咸丰年间,形成高潮,光绪以后逐渐扩大。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式实行放垦,由蒙垦到放垦,是清朝政府对河套农业政策的较大改变,根据这一政策,蒙旗适当开放了一定数量的土地由汉族人民领租垦种。也由于河套地区开通渠道,大面积开始实行灌溉农业,撒籽成田,旱涝保收,常与蒙人做生意的商人也于此时,雇佣大批晋、陕北部的贫苦农民租垦蒙地,投入资金,浚渠修堰,“就河引灌”,大受其益。由此,在河套灌区开发史上悄然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群体,农业开发与水利建设的投资者与组织者---地商,揭开了河套水利开发新纪元。
地商垦殖。“地商是封建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以修渠灌地、收粮顶租、贩卖粮食谋取高额利润的商人”,[2]是清晚期官办水利以前河套社会的实际主宰者。
道光五年(1825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经营的“永盛兴”和“锦永和”商号联合,共同出资在缠金(今临河境内)一带开挖了缠金渠(今永济渠前身),这是河套境内开挖最早的人工渠。缠金渠的开挖,标志着以甄玉、魏羊为代表的旅蒙商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河套地商。缠金渠的诞生,在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入套民众日益增多。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下特旨:“开放缠金,招商耕种。” 清廷下诏逐步开放河套境内的蒙地,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垦政策,并使移民垦殖变得公开合法,也为河套开渠发展提供了动力。随后,其他旅蒙商纷纷效仿缠金渠做法,乘机包租大片土地修渠灌垦,从中牟利,开始将以传统商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转向获利丰厚的以开渠垦殖为主的农业水利投资和出租土地以及雇佣长短工相结合的地商经济开发模式。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乌加河上游淤塞,北河断流,南河成为主河,导致南河水流畅旺,应河套西南高,东北低地形而形成的天然河道进水加大,能够“就河引灌”的河岔更加凸显,开挖渠道变得更为有利,因此“甫经得地,先议开渠”,关系灌区发展的天然河岔不断被人工洗挖、延伸利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地商数量也快速增加,于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河套灌区的地商垦殖发展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督办垦务的官办水利时期,地商经济的势头也渐渐消亡。
地商杰出的代表有初开缠金渠(永济渠)的甄玉、魏羊;开挖老郭渠(通济渠)的郭大义;独资开挖五大干渠(义和、丰济、刚济、沙河、皂火)的王同春,开挖长济渠的侯双珠、郑和以及开挖塔布渠的樊三喜、夏明堂、吉尔吉庆等。这一时期,地商们纷纷集资兴修水利,先后开挖的这些渠道,形成了晚清河套灌区八大干渠灌溉骨干渠系网,河套灌区水利建设已见雏形;这一时期,干渠以下支渠数量不断增加,不适应灌溉需要的河岔被人为疏导归并或接引为支渠,黄河取水口位置也能在总结治水经验的基础上被人为修整选取,各渠口进水量虽不能如愿控制但也有了基本认识;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始寻求科学开渠的技术方法、勘测设计与施工测量,开始有了对黄河水流运动规律、水文气象、水文地质等农田水利学科的研究有了粗浅认识,开始了对灌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与治水方略的系统思考,为灌区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从清代以来河套地区不断地被称为“中国之农业宝库”“诚西北之最理想灌溉区”“诚适宜农耕之地也”[3],也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各类学术团体的实地考察。河套灌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划时代,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结束语
综上,纵观中国古代史,河套灌区在长期的以“农为立国之本”“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思想的治边固疆实践中发育成长,河套地区始终居于历朝政权交融、斗争与迭移控制之下的兴盛之地。在延绵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因河套灌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的战略意义都与历朝历代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联系,河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锋的主战场,成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之所,也成为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推进了中华文明与社会革新,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发展是灌区建设的永恒主题,灌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向往是永远的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套灌区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寻求科学发展规律,经过不断的改造与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三个千万亩以上的特大型灌区之一。(王东胜 李韬)